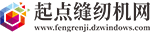【世界快播报】梦想天空下——《候鸟》制作访谈Plus
写在《候鸟》发售之后的一份个人总结
(资料图片)
(文/苍蓝的风)
大家好,我是KID Fans Club站长、原创游戏组负责人苍蓝的风,是《候鸟》的主催,主要负责了剧本部分和其他各方面的监修。
候鸟发售至今已有半个月了。说实话,现在我本人其实依然处于一个比较虚幻的状态——就属于是填了这么多年的坑,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嘭的一下,这最后一铲子土扔进去了,这个坑被你填平了,最多就是再拍几下把它拍平就行,没别的事了。
那种多年以来夙愿达成的冲击感,多少还是有点劲大的。
不过也正是这两天缓冲,让我能够认真阅读一下诸多反馈和评价,也得以进一步归纳自己这一路走来的种种得与失。
其实对于这部作品的创作历程,在游戏中的“制作访谈”项目里我大致都已经说完了,为了让大家听我絮叨我甚至还加了个成就在里面,就是为了逼迫大家的强迫症(bushi
但毕竟不能真的在那里过分地长篇大论,所以一些更多的话,一些更细节的东西,就放在这里做个总结吧!大家可以当做是制作访谈的Plus版。
先说目标。
在创作之初,也就是零几年的那个时代,同人游戏还是一个几乎不存在于国内的事物。对我来说,开这个坑多少还是带着点想要一鸣惊人的功利心——主要是给当时分家之后百废待兴的KFC论坛挣点面子、整点流量。
但是如大家所见,这坑一挖就是十多年,期间无论是日G还是国G,形势变化都称得上是沧海桑田,当年的目标早就从根本上烟消云散,反过来,随着创作的不断进行,我越发意识到了我正在做的是什么、真正想要做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在20年底将《候鸟》的项目正式公布之后,我曾针对这个问题写过一篇文章——
所以,简单来说,我的终极目标就是做出一个完全本土化的现实主义作品,除了画风不得不妥协以外,完全和日G从文化上切分开。
目前看来,这个目标算是实现了。
而除此之外,在剧本基本完成之后,我对《候鸟》其他的制作部分的期待实际上是这样的:制作一个在各个维度上都尽量没有明显短板、但又在某些方面有些长处的Galgame,换句话说,是六边形全A、争取能有一两个S的泛用型。
这个目标目前看起来也是基本上实现了。候鸟的每个维度——美术、剧本、音乐、配音、UI……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凸显的就是一个众口难调,但确实还没有哪个方向是大家一起骂的。而试图争取“S”的方面——对我来说主要是美术和配音,目前看来喜欢的人也确实多一些,还好。
囿于成本和能力所限,没法做到尽善尽美,但姑且也算是力战而竭,“我的生涯一片无悔”了。
对《候鸟》本身的期望是如此,而对《候鸟》之于国G,则是希望借此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供人参考,无论成功与否,好歹也算是披荆斩棘,做出了一点微小的开拓了。
接下来聊一聊作品的几个细项,嗯,先从我的剧本说起吧。
访谈里多少还有些语焉不详的地方,不过在这里我斗胆放飞自我一下。
首先,emmmm,怎么说呢,对于创作,哪怕是《候鸟》这样极度追求现实主义的作品,我认为核心思路也永远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我写了一个以高三、高考为核心、引起了相当一部分人共鸣的作品,对吧?
但我,没上过高中。
当然更没参加过高考。
_(:з」∠)_
可能有人说高考没参加过,那总得参加过中考吧?但我初三的时候都不太好好学习,中考上午考完试,中午骑车去网吧玩了一小时红警1,下午继续考……
所以,真的,故事里的氛围基本上都是靠我基于阅历硬编出来的。
不过编也要有编的基本法,编故事的核心思路是什么?是调动情绪,关键点抓住了,不需要很大力气就能起效果。
为啥我当年开摆了,那是因为我赶上那一波生育高峰(这个词放在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了),北京现在一年中考考生几万人,我们那一年有小二十万,以二十多年前的教育资源,高中的录取分数线被拉到一个离谱的位置,满分630,一个正常一点的高中要580,重点人均610——要说卷,什么年代都有卷的,只是具体点位不一样罢了,心理上殊途同归。
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就可以找到写作的重点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挤还是不挤,为什么挤,怎么挤,挤不动怎么办……这是人之常情,对于心智尚未成熟、难以全面权衡利弊的年轻人来说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了,再增加一些比较容易莽的冲动情绪,这些左右横跳的“犹豫”就构成了故事前半部分的主题。
最容易让玩家感同身受的部分可能也是在这里,实际上,很可能并不是我编得多么高明,但是我成功勾起了大家对往日的回忆,然后这些死去的回忆自动发起了攻击,才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故事有了,接下来要面对另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舞台。
如前所述,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虽然家庭条件普通,但那也是相对于北京这个地方的,放到全国,那就属于比较好的段位了。
原案的主要发生地,原型在甘肃,糅合了很多地方,但总之就是一个十八线的小地方。最初设定是个贫困县,但这两年脱贫攻坚战把贫困县都给取消了,只能稍微提了一点格,但还是最穷的那一档。
我没见过。
作为原案的小雨,他是兰州人,好歹是省会,那些特别穷的地方,他也没呆过。
怎么办呢?编吧。
但改编不是乱编,基本的采风得有。从09年开始,我陆陆续续去了一些地方,比如去兰州看了原案里的一些场景;借着去贵州旅游的机会,在一个景点旁边的小县城里多停留了一晚,对山城小县增加了一些直观的印象……诸如此类。
然后就是开始翻故纸堆,查资料了。
得益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很多西北地区的现状是可以直接从照片和视频里看到的;尽管我没有在那里直接生活过,但好在我岁数大,一些小时候的印象可以直接套用过来——经常说“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有XX年”,基本上按照这个年份往前推移一下,想象一下当年的基础设施,或者用大城市里老旧的一些地段,还是可以做到大致符合的。
比如百货商场这个场景,我基本上是直接拿家边上的社区百货商场来套用的,大家似乎也没觉得有什么违和:
借用“时光机”这样取巧的方式,舞台也被构建起来了。当然这也有个副作用,负责场景设计和UI设计的两位小姐姐也被我误导,以为这是一个发生在过去的故事——比较典型的就是医院的那张场景,这个暂且按下不表,后面聊美术的时候再细说吧。
好了,场面摆好了,现在该破局了。
局点在哪里呢?还是那个“不存在的东西”。
也就是,“梦想”。
《候鸟》这个项目,抛开新建文件夹时期的黑历史之外,最早确定的名字是《梦想天空下》,然后因为后来想做成一个系列作,改成了《梦想天空下~候鸟》,最后为了强调主题线索,被固定在《候鸟》上,“梦想天空”只留在了主题曲的名字里。
但无论如何改,“梦想”始终是这个故事在找到方向之后的一个核心,也是我们想要描写的重点。
叶雨潇在前面几章虽然动不动就会自动emo,但在表面上——尤其是梁芷柔面前,看起来还是特别正常的,该说说该笑笑,甚至看起来还很会撩人,只是这些都是浮于表面的,在内心之中他只会越来越积压焦虑,只是没有导火索,不会爆炸。
但是到了深秋篇,在湿地公园,遇到了比他还emo的梁芷柔,他躲不过去了。
之前的逃避导致了他只能勉强说出苍白无力的话语,那种得过且过的空间没有了,摆在他面前的路只剩下两条:要么前进,要么放弃。那种装作前进的假忙活已经骗不了自己了。
现实中很多人其实在这里是撑不下去的,但故事这样写就没有意思了,即便再怎么追求写实,文艺创作还是要高于生活的。
“高于”的点,就在于这个平时比较容易“不存在”的“梦想”。
梦想是梁芷柔的原动力,这份力量也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给了叶雨潇,最终从一粒种子开始,生根发芽、破土而出,直到故事的最后独立成材。
这也是很多人觉得后半截观感会比前面好一点的原因,因为后期开始脱实就虚,不那么直接用现实刺激人了,而且梦想不是幻想,是真的可能实现的。
最后,是结局。
结局的部分是个历史遗留问题。
在原案和最初的大纲里,结局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而是更现实、更血淋淋一点的标准结局:
终章·最后的那个夏天
放榜日。
叶雨潇还是没能考上他的第一志愿,我国的高考不是一般人只靠大半个学年的努力就可以藐视的。他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在同学中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梁芷柔成功地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不日将离开自小生长的家乡,前往东部的大城市上学。等待她的,将是一个繁花似锦,而又纸醉金迷的世界。
叶雨潇和梁芷柔又一次来到了黄河岸边的那个公园,望着滔滔江水。叶雨潇向梁芷柔道歉,说自己终究还是没有追上她的脚步。梁芷柔摇摇头,随后将头轻轻靠在叶雨潇的肩上,一直靠到夕阳西下。
我甚至特别暗示了一些牛头人老哥狂喜的设计。
这个病根源自于我在游戏里访谈时提过的那个问题:小雨写原案的时候听的是SHE的《候鸟》,我一听,说灵感取自一首叫《候鸟》的歌?我当时唯一听过的《候鸟》,是王杰的。
苦逼,太苦逼了。
标准的伤痛文学,痛!太痛了!!
所以我一开始满脑子都想的是天各一方的结局,也是这故事最早卡文的一个重要因素。
直到我看了那场电影。
虽然游戏里直接点人家名字不太合适,不过就如同一开始说的那样,在这篇文章里,不妨让我稍微放飞自我一下吧。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第一部,杨子姗那版,第50分钟到53分钟的那段剧情。
在这一段剧情之后,尤其是结合电影里黎维娟后来的结局,我的GoodEnd综合征开始集中爆发,然后开始疯狂修改故事框架。
这导致了第一版的终章直接增加了1.5万字,后来又在第二版里修改到了2.5万字,增加了5张场景、1个角色、一大段剧情,也就是……“樱华”篇。
是的,最初的计划里其实没有终章里樱华市的这段剧情,就简单在旁白里写两句话,说叶雨潇“去看了一次大海”,就交代过去了。但,现在我要强行把它加进去,开一个新地图。
开这个地图的目的是让叶雨潇找到自己的目标,真正凭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所以他需要一个意识上的升华。最初的版本基本上是让叶雨潇自己顿悟的,但后来看了看觉得太扯了,于是在第二版又开始反过来给老师、梧桐、李金凡疯狂加戏,开始通过三个不同的视点、不同的感悟,这种多维度的方式来点化他。
效果似乎还行,代价是成本飙升并且机械降神,在最后强行空降了李金凡这个角色。
李金凡这个角色一开始就有人跟我提过,加一个外力来推动男主角,但是前期被我否掉了,后期不得不加进来,我一开始写得也不好。但到了第二遍修改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2019年,说实话,这个时间点上,在故事最初构筑时那种高速发展、机会遍地的黄金时期,其实已经开始过去了,躺平的思潮已经出现。但反过来说,这种愈发明显的阶层差距和逐渐固化,也可以让我在灌鸡汤的时候更加容易把握住一点。
最终,这段鸡汤毁誉参半,有人觉得这个说教过于粗暴碍眼,也有人觉得它把剧本升华了。孰是孰非,大概还是之前提到过的那个原因——每个人代入的位置不一样,结合自身经验得到的感受也就不一样,发起攻击的,其实是现在的你自己。
故事设计的部分基本上就说到这里了,不知道读到这里的小伙伴会不会幻灭?
当然,“不存在的东西”,其实也并不是真的不存在。
尽管我完全没有过故事里的那些经历,但我可以把我看到过的类似经历抽出来,改头换面一番,再填回去,一如毕加索画牛,即便是简简单单的几条线,牛还是那个牛,在这几条线的基础上画另一头牛,也是可以画回去的。
把握住核心要素,护住最根本的逻辑关系,这是我的写作思路。《候鸟》的很多设定其实不完全基于现实,比如老家是甘肃好几个地方的糅合,而樱华也不完全是杭州,起码杭州不直接靠海对不对?我看到有些评价在极其严苛地对两边的大学分布及分数线进行考据,但其实这些细节设定是抽象的,是为了推进剧情而设计的工具,游戏/故事不是纪实/传记,追求代入感也并非追求完全无误的真实性,否则我还改地名干嘛,直接点名道姓过去不好吗?
所以会让你在故事中产生代入感和真实感的核心要素是什么呢?
是逻辑真实。
只要逻辑自洽,让人觉得这种情况确实是可能发生的,那就足够了。原型地不选在北京上海,而是特意挑了这样一个教育资源特化的城市,是为了增加这种逻辑的说服力,但并不是就说必须得完全直接照搬当地的分数线,分数线依然还是我根据剧情需要微调过的。
然后再补充一点与剧本相关的话题。
其一:劝学。
俗话说,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叫错的外号。
《候鸟》的Steam评论区里铺天盖地全是“电子劝学”的感叹,怎么说呢,其实我最初写剧本的时候是很担心的,毕竟谁玩Galgame是为了看别人做题啊?但不写又不行,学习是贯彻整个游戏的重要内容,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写,然后尽量调整相关桥段出现的节奏,避免过于沉迷学习而使得过程无聊。
但这个时候,致命的问题出现了——
我是学渣。
这一次,“不存在的东西”是真的不好画了,在原案阶段,这俩人是文科生,但文科生想找一个收入不错的工作是比较困难的,至少比理工类的专业要麻烦得多,从故事背景的角度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改掉了。
作品里讨论题目的时候用的大多是数学题,我去查了一下高中的题库,发现题我都读不懂,更别说安排在剧情里了。而如果完全虚着写呢?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那真实感一下子就拉了,从写作技巧来说,能不这么做就尽量不要。
好在,这个时候,制作组里天降救星:木之因为汉化《君が望む永遠(你所期望的永远)》而加入了我们,又对原创Gal深感兴趣,于是我们一拍即合。他是清华和东大的博士,处理这些小问题自然是手到擒来。
所以大家看到的作品中的题目部分,基本上就是我从网上搜索真题,交给木之审核无误,然后按照对话习惯把题干改写成口语阅读方式,我再交给CV酒儿去配音。我不知道自己写的是啥,酒儿不知道自己念的是啥,我俩大眼瞪小眼,一对儿睁眼瞎,但总而言之,还是顺利把这些段子给整完了。
学习经验,包括梁芷柔的一些做题表现就基本直接照搬木之的原话了。按照他的说法,“这些东西正经是对学生们有用的。虽然我们只是做galgame,我确信这些东西比很多状元讲的有意义多了(汗)。”
毕竟是参加过全国数学竞赛并且排名前列的大佬,我觉得还是值得相信的。
所以,电子《劝学》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真的可以劝学的,虽然终究不过浅尝辄止,不过至少没什么坏处。
古有白学,今有劝学,无非脱宅,何乐不为?
希望大家都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吧_(:з」∠)_
其二:甜戏。
《候鸟》中的甜戏数量比较少,整段的就暑假和春节的两段,其他基本上都被分散成日常的一些小情绪了。
这倒不是写不出来,毕竟这次我不需要画“不存在的东西”了,我是真的有老婆的,三次元的,不是纸片人老婆。
而且我俩感情还挺好的嘿嘿嘿嘿,纯发糖的日常段子我闭着眼都能写。
但是故事中没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展现这些甜戏了,想了想,再多塞进去会比较扰乱整体节奏,遂作罢。
如果有机会做DLC,我再补吧,保证全员糖尿病晚期。
真的,CG的参考图我都找好了。
其三:文学性。
在Galgame里讨论文学性似乎搞错了什么,但由于《候鸟》是个现实主义的作品,某种意义上大家对她的评价也并非是基于二次元的,所以天树虚字的豁免机制在这里是并不完全适用的,我觉得我还是得正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毕竟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剧本写得不太像是Galgame。
如游戏制作访谈中所言,其实到了后来,我已经是在用写传统文学的方式在写候鸟的剧本了。除了把它的格式适配到NVL之外,本质上来说,这就是一本青春励志风的校园小说。
那么,区别在哪里呢?
价值观。
我们小时候上语文课的时候,总要去做阅读理解,并回答文章的“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是什么。主要内容是个作品就能总结,但“中心思想”就很微妙了,这玩意真不一定是所有的作品都有的。如果是一个废萌作品,通篇下来只要人物鲜活可爱,那基本也就合格了。故事?内涵?去彼娘之,扎布多德勒。
但剧情作,尤其是现实主义的剧情作,那追求的东西就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了,《候鸟》是真的需要讨论这个问题的。
所以,《候鸟》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
虽然我很想说哈姆雷特,说鱼眼里闪着诡异的光,说我就是一个臭写剧本的我懂个屁的候鸟……但这样不好,对作品的超出作者的解读,往往是因为作者在写作时下意识地依照逻辑——或者自己的经历、三观——推演出了什么剧情,他自己可能司空见惯没有意识到,但这些东西确实不能简单归于过度解读,还是应该多说两句,起码是正面回应一下:
《候鸟》想要表达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好的,天被聊死了,但事实如此。
可能有些人觉得过于主流,过于传统。我甚至在评论区里见到一位老哥的长评,他长篇累牍地对当代教育体系表达不满,对价值观在高压下异化成了单一的“价格观”的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且对我未能进一步深刻地揭露社会问题,未能更多元化地定义“成功”而表达了失望。
我懂。
我怎么会不懂?我生活在北京这样的超一线城市,从小到大几乎完全生活在社会上升期,抛开疫情的这几年,对未来的预期始终是正面的,哪怕是最近几年,也因为我不虞失业,没什么危机。
除了岁数偏大,即便我再怎么想说自己普通,我他娘的高低也得被归在“后浪”的那一撮里。
但也正因为此,比较幸运,我不是那些“年轻”的后浪。即便出身在北京,即便祖上三代根正苗红,即便北京是全国基础保障最好的首都,我小时候也经历过因为分不到足量的牛奶配额,仅有的一点牛奶还因为家里没有冰箱,导致变质喝不了,哇哇大哭了好一阵的事。
我会尽量控制自己不要说出“何不食肉糜”的话。
多元化是好事,我以后也会制作类似的作品,我作为一个百合党,下一作就会做两个妹子贴贴的废萌小短篇调剂一下心情。
但你和西北地区穷山沟里的孩子说:
……だが、断る。
不知不觉已经水了好几千字了,我写剧本的时候要是能写这么快这么流畅就好了(bushi
总之,剧本方面的内容也说得差不多了,那么就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聊点别的。
接下来继续说美术吧。
美术的部分与剧本创作相反,对于一个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来说,需要的是画出(真的是画出)“真实存在的东西”。
视觉小说之所以是“视觉”小说,就在于它用更加直观的画面替代了很大一部分文字表述。有趣的灵(ju)魂(ben)需要花费时间来了解,好看的皮(mei)囊(shu)可是先声夺人的,而且很容易影响读者的第一印象,可以说是Galgame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所以问题来了,《候鸟》应该通过怎样的美术来塑造玩家的第一印象呢?
我的选择是——女主角梁芷柔的校服。
一直以来,国G的女生校服都有一个微妙的、几乎是约定俗成的规则:水手服/小西套。
款式多种多样,美轮美奂,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日式百褶裙。
诚然,日本是Galgame的发源地,现代二次元(不是说广义上的动漫游戏)的定义权在他们手里,日式校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拿出来就可以用,非常方便,所以大家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再正常不过了。
只是,从来如此,便对么?
无意批判,尤其是我也并非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最初的时候,梁芷柔也是一个标准的水手服妹子。在2010年第一次进行角色设计的时候,她是这个样子的:
而如果我当年行动力突然爆种,在那时候就把游戏做出来的话,大概,你们会看到这样的CG:
其实也蛮好的,起码放到当年来说,效果也算不错了。
但当年卡壳了,没做出来,然后随着2013年我意识到自己的方向有问题、开始全面转向现实主义以后,关于美术素材的风格该怎么定,我犹豫了很久。
我当时已经在考虑使用更加写实的、中国式的校服,但前无古人,我担心效果问题。
直到2014年,我看到了一部国产动画的样片:
卧槽。
卧槽!
就是这个!我他娘的要的就是这个!
不用再犹豫了,后续的人设全面转向国产的面口袋校服。在几经调整之后,梁芷柔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是梁芷柔在第一版剧本完稿时做的人设稿,大方向基本已经定型了,后续的约稿都是在这张人设稿的基础上绘制的。
这个时候已经是2016年了,本来很多原画的工作应该是在这个阶段就开始的,但人物画师因为工作压力日增,精力逐渐不足,最终在断断续续又做了一些人设之后,终于在2019年我改完稿子的时候,明确地告诉我他没有办法继续跟进这个项目了。
这是我当时身边最后一个比较能画的朋友了,无奈之下,我只能全面转向商业约稿。
中间踩了个雷,第一次约的画师画人物立绘还凑合,但CG崩得惊天动地,无奈弃之;而重新开始约稿之后,终于遇到了现在的画师九九一木,他的画册里有一张图,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球:
他画场景也是没问题的,人物立绘和CG可以都交给他。
唯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报价。其实他报的价格相对水平来说并不贵,但是在这之前我们一直都还处于半同人社团的制作思路,并且多少受到早年日G黄金年代时期剧本优先的影响,当时考虑的还是用比较低的成本做出一部以剧本为主、画面辅之的NVL来,现在骤然转向高成本,一时间有些犹豫。
但我和小雨讨论了一下,觉得钱包还算支撑得住,再说花了这么久,费尽心力写出剧本来,时间成本早就无法计算了,既然投入了心血,干嘛不做得更完善一点呢?
于是下定决心,《候鸟》也就有了现在的人物美术。
说完人物,再说背景。
作为故事舞台的直接展现,游戏中的场景就更要做到符合实际了。
比如教室,在大多数日G之中是单列的,这符合日本学校的习惯;但在国内,通常情况来说还是会设置成双列,“同桌的你”便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诞生的专有名词。而对于高三学生来说,桌面也肯定不会是干干净净的。这些要点,在最近几年的国G之中已经愈发常见,但对于当初的我们来说,还是需要探索的内容。
场景是从2016年也就是第一版稿子写完的时候开始准备的,当时绝大部分的场景都已经定下来了,但没有人会画,只能找外包。那个时候网上也没有米画师之类的约稿平台,我在微博翻腾了好几天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位看起来很棒的建筑画师:
这个阶段我们对美术的定位还比较含糊,水彩手绘虽然有点反传统,但未尝不是一种特色,画师三水猫酱是西安美院出身,基本功绝对扎实,最后我们成功开始了合作。
合作还算顺利,比如第一次约的教室场景,在我拿出了参考图以后:
画师很快给我出了稿子并细化成型:
最后的成稿效果:
感觉还不错,于是我们顺利地合作了下去。
中间有一年多她回老家结婚生孩子去了,拖了一阵子稿,但是那时候我也在修改剧本,对时间要求得并不紧,就这样慢慢搞定了《候鸟》的所有场景。
大多数场景我都很满意,只有县城的鸟瞰图大返工了一次,她很好说话,专业水平也过硬,这段时间让我充分锻炼了自己的约稿需求撰写技巧。
当然,要说问题也不是没有,最主要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她似乎误会了作品的时间点,总觉得故事原案是零几年的事情,那场景也就应该朝着早些年来靠拢——我努力扳了好几次,大多数的地方都给收回来了,但还有一些地方我自己也没啥经验的,就没控制好。
比如最明显的就是医院这张:
太古早了,现在仔细想想,这暖壶、饭盒、茶缸和脸盆都已经不是零几年能止得住了,怕不得是再往前提个十几二十年才对……但因为这些东西我是真的都见过、用过,一时间也没反应过来,就这么采用了。
总之,场景画完了,然后又给故事的每个小章节点画了转场图:
这部分转场因为后期素材和剧本都进行了一定调整,最终被大幅简化掉了,不过被利用在了成就系统里,也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些邮票。
场景画完了,然后如前所述,原定的人物画师画不了了,继任者画出了邪神,最后导致我们加钱换成了现在画师,然后……
发现画面揉不到一起去了。
人物是标准的日系板绘,色彩的运用已经不是前面两任画师那样相对比较简单的赛璐璐了。场景和人物单拿出来看都没问题,合在一起怎么看怎么奇怪。
咋办咧?难道只能换人?把前面的都换掉?我和制作组的成员们沟通了一圈,大家意见不一。
不过兼容问题实在是过于显眼了。尽管组里也有一些人非常喜欢这套手绘的场景(实际上我自己也很喜欢),但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场景统一到板绘上面来,最终,我们通过米画师成功找到了现在的场景画师aaaaki。
aaaaki是非常擅长使用光影的场景画师,他的作品通常都会带有重度的光污染,比如展现的例图是这样的:
他之前看到过我们发布的坑讯公告,对于合作很有兴趣,于是场景的重绘开始了。
经过重绘后的场景自然是改头换面了,直接RTX ON:
除此之外,对于一些旧稿中不尽人意,或者因为剧本调整而不再完美适用的场景也进行了重绘,非常尽心尽力。
改稿断断续续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当然成本也随之而来产生了大爆炸。不过都到了这个阶段了,经历过人物画师连续变动的我们已经开始有点上头了,在沉没成本的影响下,开始不再那么精细地控制预算。只要能够切实提高作品素质、报价在合理的范围、而我们又出得起这笔钱的话,就该花花吧。
所以,后来的制作人们,如果你们能看到这里,千万记住我们的惨痛教训,尽可能提前做好项目规划,不要到了后期陷入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失控局面。
UI的负责人拾九子是我们在第二稿剧本修改完成时招募到的,当时的需求是要适配旧版的美术素材,所以她绘制了比较偏手绘风的UI界面。
拾九子对需求的理解力非常强,很轻松就get到了我想要的方向,并且很快就画出了非常有感觉的成品。而且,即便在后期美术素材大幅变更,和原本风格已经完全不同的情况下,UI依然可以做到良好兼容,不得不感叹专业美工的职业素养。
当然,由于最初提需求的时候,场景还是用的旧版,导致她在画图的时候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被带得歪了一些,也开始追加老物件:
总的来说,整套UI的处理非常贴合主题,没有那种工业化的味道,很舒服,这也是我最省心的一个方面了。另外拾九子还帮我处理了很多平面美术方面的事情,对于一个完全不会使用PS的人来说,真的是救我狗命_(:з」∠)_
然后,聊一聊音乐。
音乐是个比较微妙的点,对于国G来说,音乐通常既不容易出问题,也不容易出亮点。
《候鸟》的BGM最初规划得不多,主要是春夏秋冬四首季节曲、喜怒哀乐四首情绪曲,再加上主题曲和主题曲的钢琴版,一共10首。结果,在后期写演出时,发现完全不够,不得不又另外紧急补充了7首,主要是包括两首梁芷柔的theme、两首日常theme、一首回忆、一首紧张(打架专用)、一首樱华大学theme。
BGM总的来说追求的是稳中向好,目前看来除了表达“怒”的《悬而未决》有点用力过猛了之外,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而对于主题曲《梦想天空》,我们则是多花了一些心思。
这首曲子的词曲编写时间很早,大概在2010年初就完成了——当时,shin在认真研究了我们的原案和大纲之后写出了歌词,然后交给了作曲的C.C.,后者只花了半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曲子的编写并出了DEMO,后来的正式版编曲都是在这个DEMO的基础上完成的。
C.C.无疑是个才华横溢音乐人,当时他愿意无偿帮我们制作音乐,不过需要我先把剧本写完,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所需的情绪。结果非常遗憾,我把这个坑拖得太久了,最后等我终于把剧本初稿写完时,C.C.已经退网失联了,尽管之后也曾多方寻找,但至今仍然没能联系上他,这也是《候鸟》制作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遗憾。
再次强调,大家做项目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并且及时填坑,千万不要学我啊!
总之,词曲编都做好了,现在该唱了。
这个主题曲最初的时候其实是准备找个妹子来唱的,实际上一般来说Galgame的主题曲也都是妹子唱的。但在2010年词曲刚弄好的时候,我们找了论坛上几个熟悉的女生来唱,发现那个味儿怎么都不对,仔细一想也是,整个词都是以男主角的视角来写的,女生来唱肯定是不太对劲的。然后这个事就暂时拖下去了,毕竟那时候连正经的编曲都没做,大家只是拿DEMO试了试音。
到了2020年,所有的素材都开始进入制作,主题曲的伴奏也顺利完成,那么演唱也就被提上了日程。由于我和小雨都是破锣嗓子,唱歌属于全是感情、没有技巧的那一类,所以还是只能从外面找人。
歌手这个圈子我就更是两眼一抹黑了,试探着找了几个半专业歌手,要么风格不合适,要么报价太离谱,最后只好缩回来,到B站音乐区去翻列表。
最后我们联系到了灵溪镇的清珏,他是一位声音非常干净、纯粹的歌手,与这个略显青涩的故事极为相符,于是,《梦想天空》这首歌就成为了他的第一首原创歌曲。
不得不说,这是一次非常完美的合作。在游戏最后的演出中,我想方设法掐了时间轴,让梁芷柔在说出“我,在那里……等着你。”的时候,歌曲的歌词正好也走到了“谢谢你为我许下彩虹彼端的约定”这一句,目前看来效果非常好。
接下来到了比较重头戏的一个方面,配音。
受限于剧本台词、网配CV的基本功,以及缺乏配音导演指导等诸多因素,国G配音的平均水平一直以来都比较尴尬。
台词是首先也是最主要的问题。国G很多作品都是剧本兼任主催,然后这些剧本兼主催又大都是玩多了日G以后燃起的创作欲,再然后,他们很多人可能并不怎么懂日语,玩的日G都是汉化版,这些汉化版的质量么,嗯,呵呵。
对于翻译来说,即便逐句逐词地对翻译文本进行校对润色,尚且不能保证信达雅,何况并不是每个汉化组都能做到。无论民汉官汉,稀奇古怪的翻译腔从来没有断绝过,而被这些翻译腔所毒害洗脑的玩家们,写同样类型的文体时,自然也就容易被改变成日文的形状。
当一个配音演员面对着满屏的“なら”“みたい”“それより”“かも知れない”句式,开口就是“呐”“嘛”“诶”,然后自己也气息乱、丢情绪,甚至重音都读不对,尤其是还没有人来纠正这一切的时候……
惨哪。
而且这种情况是不一定能够通过经验的增加逐渐改善的。如果一个剧本作者或者配音演员——我甚至已经不太想用“作者”“演员”来称呼这类人了——喜欢躺在自己的舒适圈里,每天依靠着旧粉丝的赞美,或者一些什么盘外招来维持着自己的形象,而不去精研业务技能的话,那无论他/她的名气如何响亮,写/配过多少作品,最后的产出都依然摆脱不了前面说的那种悲惨的水平。
《候鸟》在写作初期,大概是08、09年的那个时候,也多少沾点日式的味儿,不过等到正式找到方向以后,相关的台词全都大修了两遍,基本上消灭了日式语句,并且尽可能地做到了说人话:我在写作的时候会自己先出声念台词,感觉顺畅了再落于纸面;写完一章稿子之后,会请一到两个朋友逐字逐句地出声念一遍给我听,然后我们一起找出其中别扭的地方进行修改;最后到了实际配音的时候,也把权力直接放给配音演员,在不改变句子主要意思或者关键字眼的情况下,以他们念着舒服为标准,我可以在后期再把文字校对回实际的语音。
台词解决了,但是《候鸟》在开始挑选CV的时候出了一次巨大的问题。
大概是在第一稿剧本快要写完的时候,我们通过仅存的人脉找到了一位当时在国G圈子里耳熟能详的CV,说实话对方答应的时候我们是很兴奋的,那时候对配音圈子也没啥概念,就觉得既然是如此知名的大佬,那这次肯定稳了,于是纳头便拜。
大佬很有高人范儿,指出了我这个剧本的种种无聊之处,觉得没意思,不真实,建议我再改改。
也不能说不对,第一版稿子我自己也很不满意,要不然后面也不会逐句逐字地改了三年。无论如何,改完之后我又找到了大佬。
其实第一次大佬提出的地方我没改多少,改的都是别的东西,不过这一次大佬倒是一口答应下来,没有再提剧本水平的事,然后……失联了。
是真的失联,我能看到她正常发微博,还在发玩游戏的感想,但是不理我,发消息不回。
一个月以后,大佬再次出现,告诉我她把之前的剧本存到别处了,让我再给她发一遍。
我心态崩了。
能力如何姑且不论,态度就先有问题,作为一个上班很多年的社会人,我的内心之中开始疯狂告警。
实际上到这个时候为止,我还没经历过人物画师的二次换人,成本还没有失控,对《候鸟》的配音计划也只有梁芷柔一个女主角有语音,但我之前过分盲信名声,没做过任何试音,就直接把配音人选黑幕给这位大佬了,结果事到临头,发现并不靠谱,于是只剩下一脸懵逼。
痛定思痛,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决定把之前逃掉的课给补回来,从试音做起,而且不能只找这大佬一个人,得多找配音演员来筛选。
结果,当我把决定通知这位大佬的时候,她愤怒地指责我是因为私人关系所以才想把这个角色的位置交给别人,是配音圈里常见的黑幕,她身经百战见得多了,什么样的幺蛾子没见过?
天地良心,我一个从汉化圈子转到原创的萌新能认识几个CV啊?总之,因为这个问题,我俩大吵一架,这一吵就连续吵了三天,不过总之最后大佬还是接受了试音要求。
得亏有这次试音。
通过各种关系,以及关系的关系,我好歹找到了几位愿意来试音的配音演员,拿到了包括那位大佬在内的所有试音稿。然后,我听完以后,咳。
当时的我在配音行业确实是纯萌新,但我也没想到大佬能给我这样一份试音稿。
通知大佬结束合作的时候,她已经算是冷静下来了,比较平和地接受了这个结果,但主动开口找我要了一笔试音费。
后来我听说,就算是把业界最顶尖的那几位配音演员叫来试音,也断然没有试音费这么一说,但我当时是萌新,真的是萌新,真的。
总而言之,酒儿在这一次试音中脱颖而出,她是直接拿湿地公园梁芷柔心态崩溃的那一段来试的,当时就震撼到我了,而事实证明,选择酒儿是一件无比正确的事。
后来,每当《候鸟》公布一些消息的时候,因为国G圈子比较小的缘故,七转八转之后总会转到大佬的首页,结果就是她也会同步在她自己的微博里暗搓搓地发一些粉丝可见的碎碎念,然而她甚至没有拉黑我,每一条我都看见了。
就很典。
总之,通过这件事,我学到的教训就是试音选角这个环节一定要认真做,名声可以加分,但一定不要保送。
好的,到此为止,《候鸟》在制作过程中的大多数经历就都讲述过了。不过,在文章的最后,我还是想再多说两句关于“本土化”这方面的话题,也算是为这十年来的执念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在《候鸟》剧本正式启动的2013年,国G其实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那时候的我已经玩到了《赤印》,玩到了《雾之本境》,玩到了《鸑鷟》,在《候鸟》内测期间可能有一些朋友看到过我用来替代未完成素材的占位图,那个“你看到了一张CG”就是在仿《鸑鷟》当年的故事:
以当年的资源,同人游戏能做出来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了,内容什么的只要不是太过离谱,大多都能包容。然而,对于已经在Galgame圈子里摸爬滚打了十来年的我来说,总还是不满足的。
在制作《候鸟》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反思这个问题的原因所在——因为实际上第一稿剧本我也写过不少一看就很日式的内容,包括台词,也包括桥段。这些东西,有些是当场就发现了,有些是第二稿的时候改掉了,还有极少数漏了过去,至今残留在作品之中。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包括制作者和主要玩家受众群体——都是被二次元文化驯化过的人,而现代二次元文化的定义权,在日本。
这里说的二次元并非是指广义上的“动漫游戏”,而是带有鲜明日系特色(如OTAKU)的那套亚文化。很多人是跟着日本的ACGN一起长大的,非常熟悉这一套内容,熟知每一类角色的萌点,在出现经典桥段的时候可以会心一笑,并且跟着新番的播放,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库,最终实现对这套文化的硬解码。
而当他们中的某一些人在转换为创作者的时候,也就往往会照着自己已经熟悉的那套解码标准,反过来采用了与之完全兼容甚至相同的编码规则,而玩家也很容易就认可这套规则——实际上Galgame本身几乎完全就是二次元文化下面的一个子集,它的受众先天具有硬解的能力,读起来自然也就毫无压力,所以这套模式一直都行之有效。
本土文化在这方面非常弱势,我们在外面的二次元刻板印象是旗袍包子头会功夫,内部产出的“传统文化”类ACG作品则要么是仙侠、要么是武侠,总之多少得沾点5000年悠久文化的古风味儿,对于近现代以来的文化体现得非常少。
是真没得可写吗?
其实不是。作品不是非要宏大、曲折,或者加上什么超设定超展开才能写的,即便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写出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这在传统文学里非常常见,影视题材之中类似的作品也不少,但放到二次元,似乎大家就都觉得遥远了起来。
其实制作的时候我也经常惴惴不安,总觉得未必能获得大家的认可,实际上,《候鸟》在之前宣发时最常见的反馈就是“太扯了,我的高三一点意思都没有”。
不过,纵使前无古人,我觉得终究还是得有个头铁的来尝试这么一下,所以《候鸟》还是一路坚持着做下来了。
这是微小的一步,也是我对本土文化这个大命题交出的一份答卷。
《候鸟》的本土化当然是用了非常取巧的方法,我尽力调用了大家的共同记忆——既有高三、高考这样的特殊时刻,也有因为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各种压力,可以说是无差别覆盖轰炸了。
实际上,哪怕我在结局给了大家一个GoodEnd,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也依然是一把可以勾起回忆的刀子。
梁芷柔给叶雨潇的诅咒,当然没有作用到叶雨潇身上,但却在很多玩家身上生效了。
毕竟,谁没有点遗憾呢?
写的时候我其实没想这么多,这是我在《候鸟》发售之后,看到评论区里那许许多多结合自身经历写出的长评时,才意识到的一件事。
也算是我眼中闪起的诡异的光了_(:з」∠)_
总之,对于《候鸟》,我主要想聊的东西基本就都在这里了,全文共有将近15000字,差不多有十分之一个本体的长度了。不禁再次感叹,如果我能稳定到这个码字速度,这玩意儿我哪用得着写个三年之后又三年啊(╯‵□′)╯︵┻━┻
感谢你能够耐心挺一个老人唠叨这么久,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候鸟》的制作周期非常漫长,期间既有拖沓卡文的煎熬,也有踩坑浪费的挫折,还有参加游戏评选结果提交了试玩版人家根本不屑下载的羞辱,如果没有诸多小伙伴的鼓励,我是断然无法把这部作品成功做完的。
再次感谢!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未来的作品。
让我们下次再见!
- 【世界快播报】梦想天空下——《候鸟》制作访谈Plus
- 世界信息:齐鲁银行业绩快报:2022年归母净利35.87亿元,同比增长18.17%
- 班主任班级工作计划(实用24篇) 环球即时看
- 天天看热讯:金山软件北京办公区开工:雷军现场发红包 称会坚持“技术立业”
- 【世界时快讯】不是云南也不是海南,这个省凭什么春节游客量全国第一?
- 吴用的故事情节概括300字_吴用的故事 概括_250 mdash 300
- 二战重建者修改器(怎么用)设置能力点,设置金钱,设置砖块,设置木柴,设置碎石
- 养老机构医护人员筑牢安全屏障 守护老年群体健康|微头条
- 春节假期山东社会安全稳定治安秩序良好
- 《红霞岛》联合开发商和索尼合作 开发《地平线》系列